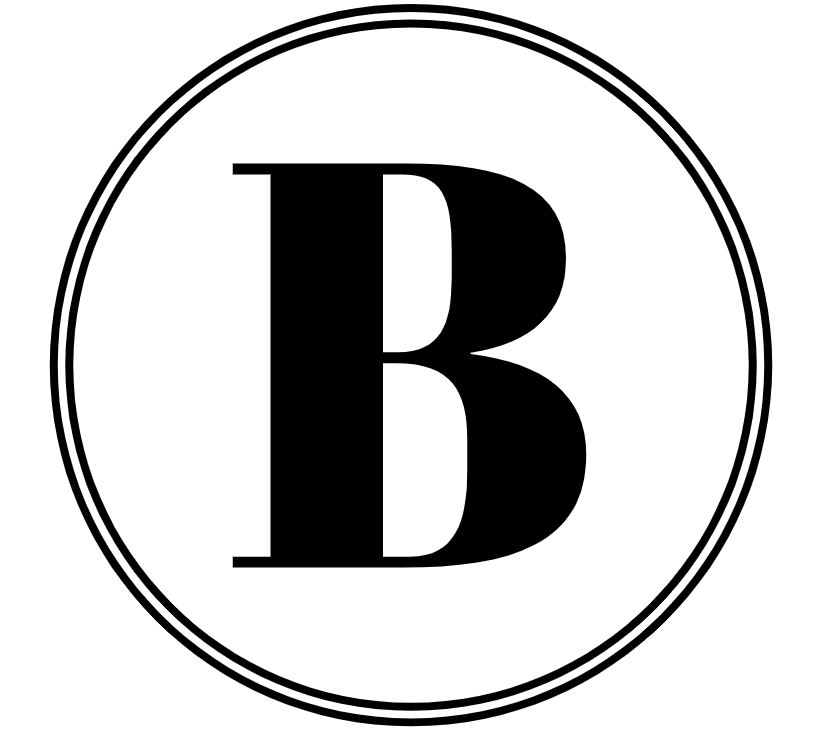如何给宝宝起名
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名字。对绝大多数人来讲,名字是要用一辈子的东西,所以一个好的名字是父母送给小孩第一件终生受用的礼物。评价一个名字好不好有很大的主观成分,但好的名字也有许多客观的共性。我在给我家小孩起名时,制作了一个姓名打分表,里面包含了我考虑到的好名字的要素和每项要素的分值。有了打分表,就能将名字进行相对客观的比较,从而有效平息各方在命名小孩当中的争论。在本文中,我把这些要素分享给大家,方便有需要的朋友借鉴或提前准备。这些要素中不包含生辰八字,五行八卦,因为我对那些毫无了解,也不怎么相信。